那些温柔又绝望的话语,像一根根细密的针,穿透厚重的石壁,精准地刺入裴净宥的心脏最深处。他拍打石门的动作骤然停住,双手无力地垂下,泪水模糊了视线,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。原来,在她心里,自己是那样温柔的人,而她,竟因为顾不好他而深深自责。
他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,巨大的悲伤和悔恨扼住了他的喉咙。他无法告诉她,不是她没用,是他混账;是他被愚蠢的骄傲蒙蔽了双眼,亲手将这个温柔善良的姑娘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他想冲进去,紧紧抱住她,告诉她一切错都在他,他才是那个最没用的人。
墓穴内,宋听晚轻轻抚摸着怀中婴儿柔软的发丝,眼神空茫而悲伤。她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睡颜,嘴角扯出一抹苦涩的笑容,对着还不懂人事的婴儿说着心里话。
「你们的爹很温柔,带领我认识好多事……」
她低声呢喃着,声音轻得仿佛一碰就碎。她想起了那些被他温柔包容的日子,想起了他在书局里的告白,想起了他笨拙地学着不让自己害怕的模样。那些曾经是她黑暗生命里唯一的光,如今却成了最锋利的刀,时时刻刻提醒着她失去了什么。
「但是娘顾不好他,娘是不是很没用?跟你们说这些干啥呢?又听不懂……」
墓穴外,裴净宥终于无力支撑,背脊靠着冰冷的石门滑落在地。他紧紧抱住那把被他拆开又重新组合好的鲁班锁,将脸深深埋进臂弯,压抑的、痛苦的呜咽从喉咙深处泄露出来。他从不知道,自己的存在,竟会带给她这样沉重的负担与痛苦。
这句半是玩笑半是委屈的轻问,像一柄烧红的铁锥,猛地刺穿了裴净宥的耳膜,直直烙在他的心上。他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,紧接着又疯狂地涌向头顶,让他耳鸣目眩。打?是啊,何止是该打,他该千刀万剐,该被五雷轰顶。
「但是娘很爱他,他却误会娘,你们说爹爹是不是该打打?」
他想起了那张泪流满面的脸,想起了她在地牢里望向自己的、那丝仅存的信任,而自己却用最冰冷的话语和最残酷的禁足,将那份信任彻底粉碎。他不是该打,他是该死。强烈的自我厌恶如潮水般将他淹没,他擡起颤抖的手,毫不犹豫地、狠狠地抽在自己脸上。
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山野间格外刺耳,脸颊火辣辣地疼,但这点皮肉之苦,与心中那片被悔恨撕碎的废墟相比,根本不值一提。他不在乎,只希望自己能痛得清醒一些,痛得能记住自己究竟犯下了多么不可饶恕的罪孽。
墓穴内,宋听晚轻轻捏了捏孩子肉乎乎的小脸蛋,听着他们发出无意义的咿呀声,眼底的悲伤被一丝浅浅的笑意取代。那笑意很淡,却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有了生气。
「你们说爹爹是不是该打打?」
她用鼻尖蹭着宝宝的脸颊,像是在与他们分享一个秘密。这句话带着孩子气的嗔怪,也藏着她从未宣之于口的委屈与爱恋。她只是想找个倾诉的对象,哪怕对象只是两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婴儿。
墓穴外的裴净宥,听着这句话,却像是在听着最残酷的审判。他扶着墙艰难地站起身,眼中血红一片,那里面没有了绝望,只剩下一种近乎疯狂的执念。他握紧了手中的木锁,指节因用力而发白,心里发下重誓:听晚,你等着,我会进去,你说该打,我便把自己交给你,任你处置。
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,在裴净宥的脑中轰然炸开。他刚刚站起的身体猛地一晃,脸上残存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。差点没挺过来?太爷?外公外婆?这些破碎的词语拼凑出了一个他从未敢想像的、血淋淋的真相。原来在她独自承受生育之苦时,自己竟然一无所知,还在京城的醉生梦死中怨恨着她。
一股尖锐的、穿心蚀骨的疼痛攫住了他,比任何身体上的伤痛都要猛烈千百倍。他仿佛能看到她苍白如纸的脸,看到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模样,而那时的他在做什么?在借酒浇愁,在自怨自艾。他不再是愤怒,不再是悔恨,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、对自己的厌恶与憎恨。
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死死地捂住心口,试图按住那里传来的、几乎要将他撕裂的剧痛。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了几步,直到后背重重撞在树干上才停下。他靠着树干,身体缓缓滑落,最终狼狈地瘫坐在地上,像一具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的空壳。
墓穴里,温暖的烛火映照着宋听晚柔和的侧脸,她低头看着怀中两个粉雕玉琢的孩子,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怜爱。她对孩子们的说话,早已成了她这两年来排解孤寂的唯一方式。
「娘生你们差点没挺过来,要不是太爷把我带回去给你们外公外婆救,我就看不到你们这两个宝贝了!」
她轻声说着,仿佛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说完,她低下头,温柔地亲了亲儿子的额头,又亲了亲女婴的脸颊,那样的珍爱与依恋,让她整个人都在发光。
裴净宥闭上眼,泪水顺着指缝不断涌出。他终于明白,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他亲手将他全世界最勇敢、最珍爱的女人,推向了死亡的边缘。而她,却在生死一线间,拼死保住了他们的孩子。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两年的时光,更是她用生命换来的、他永远无法偿还的恩情。
那股足以将人撕裂的悔恨过后,奇迹般地,一股异样的平静笼罩了裴净宥。他不再哭了,只是用袖子胡乱抹了把脸,然后用手掌支着地面,一寸一寸、稳定地重新站了起来。他看着墓穴紧闭的石门,眼中血红未退,但那份疯狂的绝望已被一种深沉坚定的火焰所取代。
他弯腰拾起散落在地上的鲁班锁零件,动作不再像之前那般急躁,而是带着一种近乎庄严的认真。他走回宋家书房,将木锁轻轻放在书案上,然后对着宋太老爷深深一揖,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。
「老太爷,我明白了。」
宋太老爷擡眼瞥了他一下,没有说话,只是端起了手边的茶杯。裴净宥没有再要求任何机会,而是转身走到那堆废弃的木料前,拿起工具,开始笨拙地模仿着记忆中鲁班锁的结构,一刀一刀地刻划起来。他手上的伤口还在渗血,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
他知道,单纯地拆解是没用的,听晚亲手打造的机关,里面藏着她的心思,她的恐惧,她的防备。他必须用自己的心去理解,去学习,去亲手造出能与她对话的东西。从此,书房里日夜都响着刻刀刮削木头的声音,他不再喝酒,不再昏睡,只是专注地磨练着。
宋太老爷看着他那股不要命的劲儿,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,却终究没有再说一句打击的话。有时候,人需要从废墟里自己站起来,别人帮不了,而这个年轻人,似乎终于找到了站起来的理由,哪怕那理由沉重得足以压垮任何人。
墓穴深处的机关室内,灯火通明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香和婴儿身上特有的奶香。宋听晚轻轻摇着怀中的女婴,看她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自己,忍不住低下头,用鼻尖亲暱地蹭了蹭她柔软的小脸蛋。
她擡眼看向正在专心打磨一个小木马的宋太老爷,他银白的胡须在烛光下闪着温润的光。这些日子,老人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她们母子,这份温暖让她冰封的心渐渐有了一丝暖意,也让她有了一些可以放心依赖的胆量。
她看着老爷子脸上偶尔闪过的疲惫,轻声开口,语气里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依恋与关心。这是她两年来,第一次主动询问外面的事情,也是第一次,担心起眼前这位为她遮风挡雨的长辈。
「太爷,最近很忙吗?看您一走连好几天没回来呢。」
宋太老爷打磨木马的手顿了一下,他擡起头,佯装瞪了宋听晚一眼,语气却是满满的宠溺。他总不能告诉她,自己是隔三差五跑到宋家,去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,如何像个傻子一样,在书房里拼了命地学着他们宋家的手艺。
「瞎操心什么?老爷子我能有什么忙的。就是看你外公外婆,顺便帮你那不成器的爹娘收拾点烂摊子。」
他嘴上说得轻巧,眼神却瞟向墓穴入口的方向,心里叹了口气。那小子倒是个顽石,居然真的熬了下来,手艺虽然还不成气候,但那份心性,却是磨练出来了。只是,他要修补的,可不止是一把鲁班锁那么简单啊。
她将两个小小的、温暖的身体紧紧揽入怀中,左边的儿子正不安分地挥舞着肉乎乎的小手,右边的女儿则安静地依偎在她肩头,发出满足的轻哼。这两个小小的生命是她的一切,是她活下来的唯一理由,也是她此刻唯一能够紧紧抓住的、真实的温暖。
宋太老爷看着她完全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,对自己的话语充耳不闻,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,脸上却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。他把那个已经初具雏形的木马放到一边,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椅子上,静静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。他知道,此刻的她需要这份全然的投入来填补内心的空洞。
宋听晚用脸颊轻轻磨蹭着儿子细软的头发,低声哼唱着不成调的摇篮曲。她的声音很轻,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疲惫,但更多的却是满溢而出的母爱。对她而言,只要怀里抱着这对龙凤胎,外界的纷扰与过往的伤痛,仿佛都能被暂时隔绝在这小小的机关室之外。
「乖囡囡,乖宝贝,娘在这里呢,哪儿也不去。」
她低声呢喃着,像是在对孩子们保证,也像是在对自己说。她用指腹轻轻抚摸着女儿光滑的脸颊,感受着那细嫩的触感,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触动了。这两个孩子,是她用半条命换来的珍宝,她绝不会让任何人把他们从自己身边带走。
宋太老爷看着她戒备的模样,心里轻轻叹了口气。他看得出来,她用孩子们为自己筑起了一道新的围墙,一道比任何机关都更难以逾越的墙。而墙外那个拼命想钻进来的年轻人,恐怕还有一段更难走的路要走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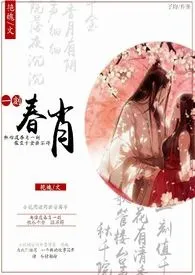


![[综]喵咪咖啡馆](/d/file/po18/706851.webp)

